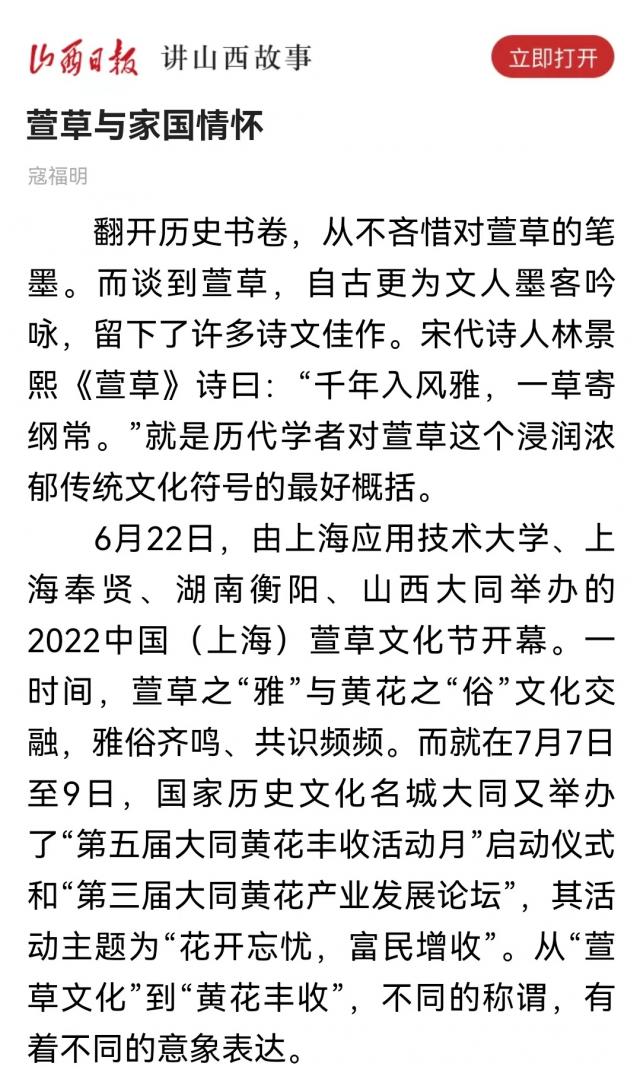
寇福明
翻开历史书卷,从不吝惜对萱草的笔墨。而谈到萱草,自古更为文人墨客吟咏,留下了许多诗文佳作。宋代诗人林景熙《萱草》诗曰:“千年入风雅,一草寄纲常。”就是历代学者对萱草这个浸润浓郁传统文化符号的最好概括。
6月22日,由上海应用技术大学、上海奉贤、湖南衡阳、山西大同举办的2022中国(上海)萱草文化节开幕。一时间,萱草之“雅”与黄花之“俗”文化交融,雅俗齐鸣、共识频频。而就在7月7日至9日,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同又举办了“第五届大同黄花丰收活动月”启动仪式和“第三届大同黄花产业发展论坛”,其活动主题为“花开忘忧,富民增收”。从“萱草文化”到“黄花丰收”,不同的称谓,有着不同的意象表达。
黄花,叶片舒展,花柄欣长,秀雅素洁,俗称金针、学名萱草、古曰忘忧,既为佳卉良药,又是可口菜蔬。当今社会,萱草以“黄花”名世,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已经远离多数人的日常生活。而通过梳理萱草的文化意象,只是希望人们观赏萱草、品味黄花时,不再陌生其背后的理想和情志,而是成为我们滋养情感和道德的新源泉。
汉代学者许慎《说文解字 f 艸部》曰:“藼,本令人忘忧之草。藼,即‘萱’之古字。”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曰:“(萱草)苗花味甘、性凉、无毒,治小便赤涩、身体烦热,除酒疸,消食,利湿热。作菹,利胸膈、安五脏、令人欢乐无忧,轻身明目。”相传,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早年贫寒患了浮肿,偶遇一位善良的黄婆婆,看陈胜胀痛难忍,就给他吃了3碗蒸熟的萱草花,很快陈胜的浮肿便消退了。这本是中医“药食同源”的案例之一,却契合了中国古代文人夹缝生存、忧生伤世、上下求索的家国情怀,成为历代文学作品的传统主题。
萱草的忘忧之意,初见于《诗经 f 卫风 f 伯兮》。诗云:“焉得谖草,言树之背。愿言思伯,使我心痗。”丈夫征战不归,妻子情思缠绵,无奈之余只能寄望萱草,借忘忧之草消除胸中郁闷。汉代经师郑玄《笺》曰:“忧以生疾,恐将危身,欲忘之。”如果说,《伯兮》之“忧”只是思妇的个人之忧,那么,北宋诗人石延年《题萱花》诗则大大丰富了萱草的文学意象。其诗曰:“移萱树之背,丹霞间金色。我有忧民心,对君忘不得。”作者感叹民生维艰、黍离之悲,关切民族苦难、国家忧患,伤世情怀无以言表,于是寄情萱草,给萱草平添了忧国忧民的厚重意义,展示了古代知识分子命运多舛又心怀天下的忧患意识。
千百年来,无数文人用这种敏感的心灵,默然体味着现实人生的感伤情绪,或者穷途恸哭,或者欢宴丧歌,或者求仙访道,诸如此类的疏狂之举,成为历代文学作品中忧愁感伤的永恒主题,也成为萱草作为忘忧草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。
在家尽孝、为国尽忠,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。《隋书 f 帝纪 f 卷三》曰:“孝悌有闻,人伦之本,德行敦厚,立身之基。”2021年,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期间,北京长安街“中共一大会址”立体花坛中,萱草成为主打花卉,默默诉说着“百年庆华诞,忠孝献慈母”的情愫。
最早把萱草与“慈母”结为一体的是唐代诗人孟郊,其《游子》诗云:“萱草生堂阶,游子行天涯。慈亲倚堂门,不见萱草花。”虽然以忘忧为主题,慈母形象却跃然纸上。《仪礼 f 士昏礼》记曰:“妇洗在北堂”,是指在母亲居住的北堂庭院种植萱草,可以减轻母亲对远行游子的思念之苦。后来,北堂植萱成了民俗,萱草就成了宣扬孝文化的母亲花。
宋代诗人家铉翁《萱草篇》直接以萱草代母,祈福慈母安康长寿,诗云:“诗人美萱草,盖谓忧可忘。人子惜此花,植之盈北堂。庶以悦亲意,岂特怜芬芳。使君有慈母,星发寿且康。晨昏谨色养,彩服戏其傍。燕喜酌春酒,欢然釂金觞。”明朝时期,理学扩张,忠孝节义空前高扬,萱草代母升格为文化现象,中华母亲花的象征意义得到进一步强化,最终内化为中华民族的群体心理和记忆。
魏晋时期,战火纷飞,瘟疫流行,企盼子嗣兴旺成为民众生活最为重要的部分。传统社会,繁衍后代至关重要。多生男孩不仅能够增加劳动力,还是家族兴盛的重要标志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曰:“(萱草)结实三角,内有子,大如梧子,黑而光泽。”正是萱草多子且容易繁衍的特点,自然就被先民视为“多子多福”的吉祥物。西晋学者周处《风土记》曰:“花曰宜男,妊妇佩之,必生男。又名萱草。”因此,古代女子不但喜欢种植佩戴萱草花,服装首饰也往往选用萱草形象以求生男。
南朝梁元帝《宜男草》曰:“可爱宜男草,垂采映倡家。何时如此叶,结实复含花。”目睹庭院中的萱草,想象着萱草花朵的美丽,倡家女子羡慕之余,又生出无限感慨,不知自己何时能够跳脱风尘,像其他女子一样结婚生子,享受家庭的幸福生活。这种孤独与失落在唐代诗人于鹄的《题美人》中更加扩展了我们的想象空间,其诗云:“秦女窥人不解羞,攀花趁蝶出墙头。胸前空带宜男草,嫁得萧郎爱远游。”秦女率真,大胆翻墙,窥探丈夫归来与否,却空留一腔的惆怅,就算自己佩戴宜男草,遇到一个浪荡不归的夫婿也是枉然。场景凄清,情韵悠长,诗中的萱草就是子息繁盛的象征,隐含着秦女对家庭幸福的满心期待。
“以古人之规矩,开自己之生面”,黄花的传统文化意象理应从多方面发扬光大,并融入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中。传播文化价值,促进萱草文化符号价值的新时代构建,让这朵全民共识的“中华母亲花”花开千万家。
媒体链接:http://sxshare.sxrbw.com/detail/paperB/187402_paperid_187402